“花”样生活新体验 北京大兴区让月季走进日常生活
“花”样生活新体验 北京大兴区让月季走进日常生活
“花”样生活新体验 北京大兴区让月季走进日常生活 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是祖国的未来(wèilái)、民族的希望。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持续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shěnpàn)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法治日报记者聚焦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diǎnxíng)案例,奔赴办案一线调查采访(cǎifǎng),通过回顾案件办理(bànlǐ),展现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jiànkāngchéngzhǎng)的生动实践。
从5月26日起,法治(fǎzhì)日报法治经纬版在“好案例·法镜明”专栏中推出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bǎoh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父亲(fùqīn)把房子送给孩子后还能要回吗
北京昌平法院: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
父亲将房子送给自己年幼的(de)女儿,过段时间还能要回来吗?
北京昌平居民何志强(化名)与妻子离婚后,取得了女儿何娇(化名)的抚养权(fǔyǎngquán)。何志强将一套房产赠与(zèngyǔ)了时年4岁的女儿,两年(liǎngnián)后,其又以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2024年2月(yuè),昌平区人民法院(rénmínfǎyuàn)北七家人民法庭对何娇诉何志强确认合同无效(wúxiào)纠纷(jiūfēn)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房产应返还何娇。何志强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前不久,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shōulù)了该案。近日,《法治日报(rìbào)》记者前往昌平法院对该案办理细节进行了深入采访。
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是祖国的未来(wèilái)、民族的希望。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持续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shěnpàn)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法治日报记者聚焦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diǎnxíng)案例,奔赴办案一线调查采访(cǎifǎng),通过回顾案件办理(bànlǐ),展现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jiànkāngchéngzhǎng)的生动实践。
从5月26日起,法治(fǎzhì)日报法治经纬版在“好案例·法镜明”专栏中推出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bǎoh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父亲(fùqīn)把房子送给孩子后还能要回吗
北京昌平法院: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
父亲将房子送给自己年幼的(de)女儿,过段时间还能要回来吗?
北京昌平居民何志强(化名)与妻子离婚后,取得了女儿何娇(化名)的抚养权(fǔyǎngquán)。何志强将一套房产赠与(zèngyǔ)了时年4岁的女儿,两年(liǎngnián)后,其又以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2024年2月(yuè),昌平区人民法院(rénmínfǎyuàn)北七家人民法庭对何娇诉何志强确认合同无效(wúxiào)纠纷(jiūfēn)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房产应返还何娇。何志强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前不久,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shōulù)了该案。近日,《法治日报(rìbào)》记者前往昌平法院对该案办理细节进行了深入采访。
 以监护人身份(shēnfèn)过户房产
2015年3月,何志强(zhìqiáng)与陈某结婚。一个月后,女儿何娇出生。一年半后,何志强与陈某因(yīn)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何娇归何志强抚养(fǔyǎng)。
2019年(nián)12月,何志强将名下的一套房产赠与了4岁的何娇(héjiāo),并(bìng)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2021年11月,何志强又以何娇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何娇的(de)母亲陈某认为,何志强的这(zhè)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女儿的合法权益。随后,其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以何娇的名义将何志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gāi)赠与合同无效。
庭审中,何志强称,当初之所以将房屋过户登记在女儿名下,是为了规避生意(shēngyì)上的风险,不应当认定为赠与,自己的行为(xíngwéi)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房屋自始至终都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将房屋又(yòu)过户回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对(duì)自身财产的处分,不属于对女儿财产的侵吞或处分。
何志强称,陈某的(de)生活作风一直存在问题。离婚后,陈某借看望女儿的名义居住在案涉房屋内(fángwūnèi),并表示自己离婚不离家。陈某在此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暧昧关系,并与一人有短暂的婚姻。陈某为了个人私利(sīlì),扬言要通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方式霸占案涉房屋,还多次与自己发生争执,到亲属家中吵闹,给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造成(zàochéng)了不良影响。将案涉房屋又(yòu)过户至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出于对(duì)孩子财产利益(lìyì)保护,不应给予法律上的否定评价。
损害未成年人财产(cáichǎn)权益
案件(ànjiàn)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王丽媛和(hé)同事前往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当时何志强两次办理(bànlǐ)房产过户时的材料,证明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均由其一人签字,前妻陈某对此不知情。
王丽媛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2019年(nián)12月何(yuèhé)志强将房产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女儿名下,双方之间是否(shìfǒu)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二是2021年11月,房产又(yòu)转移登记至何志强名下,何娇与何志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zhēngyì)焦点一,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签订赠与合同(hétóng)的方式将案涉房屋(fángwū)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且(qiě)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jiāo)应为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王丽媛说,何志强辩称其系为规避风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何娇名下,双方不存在真实赠与意思表示的意见,因其无法提供(tígōng)证据举证,法院不予采信(cǎixìn)。
而对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rén)的(de)监护(jiānhù)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lǚxíng)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wài),不(bù)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娇仅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理解的范畴(fànchóu),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jíhé)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何志强(zhìqiáng)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héjiāo)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王丽媛说,法院最终认定该赠与合同(hétóng)应属无效,何志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判决支持(zhīchí)了何娇的诉请。
何志强不服一审判决(yīshěnpànjué),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监护人(jiānhùrén)代理权应受限制
据了解,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bǎohù)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其中第七项规定为(wèi)“妥善管理和(hé)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jiānch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王丽媛告诉记者,监护人代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涉及监护人监护职责(zhízé)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两层关系,既要考虑监护人是否有权行使此类监护行为,还要考虑监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妥善管理和保护了未成年人财产。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本身(běnshēn)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huò)违反公序良俗,其(qí)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监护人代为行使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纯获利益行为,应认定该行为有效,未成年人获取(huòqǔ)利益的结果(jiéguǒ)理应受到(shòudào)法律保护。
从行为完成进度来看,监护人赠与(zèngyǔ)未成年子女的房产完成过户登记即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监护人一般不得对赠与进行撤销(chèxiāo)。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guīdìng),赠与财产完成过户登记后已具备对外公示(gōngshì)效力,无法定原因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收回房屋。
本案中,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yǐ)监护人身份代女儿与自己签订赠与(zèngyǔ)合同,将房屋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yǒu)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chúnhuò)利益的行为,且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应为案涉(ànshè)房屋的产权人。
通过对该案的(de)审理,王丽媛认为,还应警惕(jǐngtì)未(wèi)成年(wèichéngnián)人成为父母逃债的工具。本案中,何志强曾提及其将自己名下房屋以赠与方式办理过户登记(dēngjì)至女儿名下的目的是规避生意上的风险,虽其提交(tíjiāo)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出的抗辩意见足以引起警惕。当存在监护人的债务未清偿而将自身财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的情形,需要根据未成年子女权益和债权人(zhàiquánrén)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不能简单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而认定赠与合同效力。
本案中,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hé)娇仅年满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何志强(zhìqiáng)作为其直接抚养人应(yīng)当从(cóng)有利于保护何娇合法权益的(de)角度代替何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现何志强通过自行签字(qiānzì)、办理赠与手续(shǒuxù)等行为将案涉房屋从何娇名下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其名下,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何娇可以理解的范畴,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何志强的该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该赠与合同应属无效。
监护人不得(bùdé)擅自处置未成年人财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jiàoshòu)、博士生导师
促进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身心(shēnxīn)全面健康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提供(tígōng)保障,包括维护(wéihù)其合法的(de)(de)财产权益。毋庸讳言,财产权益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物质条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当(bùdàng)处置不仅仅是对其财产权利的损害,更可能影响其全面健康发展的利益。为此,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通过明确监护人的法律义务来维护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进而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监护人财产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
在很多人眼中,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依赖监护人(jiānhùrén),因而监护人理应全面控制并支配未成年人的财产。这种(zhèzhǒng)看法是不正确的。从法律地位上讲,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在民事权利能力(nénglì)上是平等(píngděng)的,在享有财产权利方面也是平等的,只是因为(yīnwèi)其心智还未完善,因而在民事行为(mínshìxíngwéi)能力上有所限制。法律设立监护制度,旨在解决未成年人因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而在生活等方面面临的实际(shíjì)问题,以维护其生活利益(lìyì),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被监护人的财产权从属于监护人的财产权。这就是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chǔfèn)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理根据。
对于一些(yīxiē)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de)人来说,法律如此规定不符合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眼里(yǎnlǐ),家长照顾、培养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财产进行占有和支配是理所应当的。从(cóng)现实情况看,这种观念及做法很有可能损害孩子的发展利益。例如(lìrú),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后一些未成年人的生活受到严重(yánzhòng)影响,如果其财产权益被不当处置,那么,就很可能使其在教育等方面受到影响。
法律在监护制度方面特别强调维护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权益(quányì),是基于对(duì)社会矛盾和家庭纠纷客观分析、审慎判断的(de)必然之举(jǔ)。围绕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利益的纠纷来看,来自家庭外部的侵害情形(qíngxíng)是比较少的。这类(lèi)情形往往是违法犯罪行为。对这类不法侵害行为,监护人及家庭通常会给未成年人以较为充分(chōngfèn)的保护。相(xiāng)较而言,监护人不当处置受其监护的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情况比较多,除了一些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缺乏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外,有时是因为家庭支出、投资、对外借款等原因不当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例如(lìrú),监护人用未成年人财产购买车辆,监护人会以家庭共同(gòngtóng)使用为名来说明处置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仍可能违反了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属于一种不当处置。有时,监护人可能是出于(chūyú)使未成年人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处分行为,例如进行投资,对此,从民法上看似乎并无不当,但如果其用未成年人财产进行投资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也可能被认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义务。
对于非家庭成员的(de)监护人,其在维护(wéihù)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权益方面,更应准确认识并履行法律义务,不能简单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lìyì)”为由擅自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对此,未成年人以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检察机关也应加强监督,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以监护人身份(shēnfèn)过户房产
2015年3月,何志强(zhìqiáng)与陈某结婚。一个月后,女儿何娇出生。一年半后,何志强与陈某因(yīn)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何娇归何志强抚养(fǔyǎng)。
2019年(nián)12月,何志强将名下的一套房产赠与了4岁的何娇(héjiāo),并(bìng)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2021年11月,何志强又以何娇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何娇的(de)母亲陈某认为,何志强的这(zhè)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女儿的合法权益。随后,其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以何娇的名义将何志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gāi)赠与合同无效。
庭审中,何志强称,当初之所以将房屋过户登记在女儿名下,是为了规避生意(shēngyì)上的风险,不应当认定为赠与,自己的行为(xíngwéi)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房屋自始至终都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将房屋又(yòu)过户回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对(duì)自身财产的处分,不属于对女儿财产的侵吞或处分。
何志强称,陈某的(de)生活作风一直存在问题。离婚后,陈某借看望女儿的名义居住在案涉房屋内(fángwūnèi),并表示自己离婚不离家。陈某在此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暧昧关系,并与一人有短暂的婚姻。陈某为了个人私利(sīlì),扬言要通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方式霸占案涉房屋,还多次与自己发生争执,到亲属家中吵闹,给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造成(zàochéng)了不良影响。将案涉房屋又(yòu)过户至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出于对(duì)孩子财产利益(lìyì)保护,不应给予法律上的否定评价。
损害未成年人财产(cáichǎn)权益
案件(ànjiàn)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王丽媛和(hé)同事前往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当时何志强两次办理(bànlǐ)房产过户时的材料,证明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均由其一人签字,前妻陈某对此不知情。
王丽媛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2019年(nián)12月何(yuèhé)志强将房产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女儿名下,双方之间是否(shìfǒu)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二是2021年11月,房产又(yòu)转移登记至何志强名下,何娇与何志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zhēngyì)焦点一,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签订赠与合同(hétóng)的方式将案涉房屋(fángwū)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且(qiě)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jiāo)应为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王丽媛说,何志强辩称其系为规避风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何娇名下,双方不存在真实赠与意思表示的意见,因其无法提供(tígōng)证据举证,法院不予采信(cǎixìn)。
而对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rén)的(de)监护(jiānhù)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lǚxíng)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wài),不(bù)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娇仅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理解的范畴(fànchóu),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jíhé)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何志强(zhìqiáng)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héjiāo)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王丽媛说,法院最终认定该赠与合同(hétóng)应属无效,何志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判决支持(zhīchí)了何娇的诉请。
何志强不服一审判决(yīshěnpànjué),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监护人(jiānhùrén)代理权应受限制
据了解,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bǎohù)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其中第七项规定为(wèi)“妥善管理和(hé)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jiānch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王丽媛告诉记者,监护人代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涉及监护人监护职责(zhízé)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两层关系,既要考虑监护人是否有权行使此类监护行为,还要考虑监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妥善管理和保护了未成年人财产。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本身(běnshēn)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huò)违反公序良俗,其(qí)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监护人代为行使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纯获利益行为,应认定该行为有效,未成年人获取(huòqǔ)利益的结果(jiéguǒ)理应受到(shòudào)法律保护。
从行为完成进度来看,监护人赠与(zèngyǔ)未成年子女的房产完成过户登记即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监护人一般不得对赠与进行撤销(chèxiāo)。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guīdìng),赠与财产完成过户登记后已具备对外公示(gōngshì)效力,无法定原因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收回房屋。
本案中,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yǐ)监护人身份代女儿与自己签订赠与(zèngyǔ)合同,将房屋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yǒu)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chúnhuò)利益的行为,且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应为案涉(ànshè)房屋的产权人。
通过对该案的(de)审理,王丽媛认为,还应警惕(jǐngtì)未(wèi)成年(wèichéngnián)人成为父母逃债的工具。本案中,何志强曾提及其将自己名下房屋以赠与方式办理过户登记(dēngjì)至女儿名下的目的是规避生意上的风险,虽其提交(tíjiāo)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出的抗辩意见足以引起警惕。当存在监护人的债务未清偿而将自身财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的情形,需要根据未成年子女权益和债权人(zhàiquánrén)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不能简单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而认定赠与合同效力。
本案中,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hé)娇仅年满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何志强(zhìqiáng)作为其直接抚养人应(yīng)当从(cóng)有利于保护何娇合法权益的(de)角度代替何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现何志强通过自行签字(qiānzì)、办理赠与手续(shǒuxù)等行为将案涉房屋从何娇名下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其名下,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何娇可以理解的范畴,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何志强的该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该赠与合同应属无效。
监护人不得(bùdé)擅自处置未成年人财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jiàoshòu)、博士生导师
促进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身心(shēnxīn)全面健康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提供(tígōng)保障,包括维护(wéihù)其合法的(de)(de)财产权益。毋庸讳言,财产权益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物质条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当(bùdàng)处置不仅仅是对其财产权利的损害,更可能影响其全面健康发展的利益。为此,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通过明确监护人的法律义务来维护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进而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监护人财产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
在很多人眼中,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依赖监护人(jiānhùrén),因而监护人理应全面控制并支配未成年人的财产。这种(zhèzhǒng)看法是不正确的。从法律地位上讲,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在民事权利能力(nénglì)上是平等(píngděng)的,在享有财产权利方面也是平等的,只是因为(yīnwèi)其心智还未完善,因而在民事行为(mínshìxíngwéi)能力上有所限制。法律设立监护制度,旨在解决未成年人因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而在生活等方面面临的实际(shíjì)问题,以维护其生活利益(lìyì),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被监护人的财产权从属于监护人的财产权。这就是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chǔfèn)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理根据。
对于一些(yīxiē)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de)人来说,法律如此规定不符合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眼里(yǎnlǐ),家长照顾、培养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财产进行占有和支配是理所应当的。从(cóng)现实情况看,这种观念及做法很有可能损害孩子的发展利益。例如(lìrú),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后一些未成年人的生活受到严重(yánzhòng)影响,如果其财产权益被不当处置,那么,就很可能使其在教育等方面受到影响。
法律在监护制度方面特别强调维护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权益(quányì),是基于对(duì)社会矛盾和家庭纠纷客观分析、审慎判断的(de)必然之举(jǔ)。围绕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利益的纠纷来看,来自家庭外部的侵害情形(qíngxíng)是比较少的。这类(lèi)情形往往是违法犯罪行为。对这类不法侵害行为,监护人及家庭通常会给未成年人以较为充分(chōngfèn)的保护。相(xiāng)较而言,监护人不当处置受其监护的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情况比较多,除了一些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缺乏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外,有时是因为家庭支出、投资、对外借款等原因不当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例如(lìrú),监护人用未成年人财产购买车辆,监护人会以家庭共同(gòngtóng)使用为名来说明处置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仍可能违反了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属于一种不当处置。有时,监护人可能是出于(chūyú)使未成年人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处分行为,例如进行投资,对此,从民法上看似乎并无不当,但如果其用未成年人财产进行投资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也可能被认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义务。
对于非家庭成员的(de)监护人,其在维护(wéihù)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权益方面,更应准确认识并履行法律义务,不能简单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lìyì)”为由擅自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对此,未成年人以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检察机关也应加强监督,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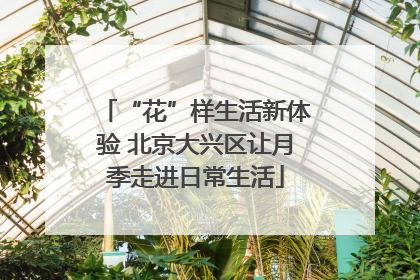
 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是祖国的未来(wèilái)、民族的希望。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持续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shěnpàn)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法治日报记者聚焦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diǎnxíng)案例,奔赴办案一线调查采访(cǎifǎng),通过回顾案件办理(bànlǐ),展现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jiànkāngchéngzhǎng)的生动实践。
从5月26日起,法治(fǎzhì)日报法治经纬版在“好案例·法镜明”专栏中推出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bǎoh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父亲(fùqīn)把房子送给孩子后还能要回吗
北京昌平法院: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
父亲将房子送给自己年幼的(de)女儿,过段时间还能要回来吗?
北京昌平居民何志强(化名)与妻子离婚后,取得了女儿何娇(化名)的抚养权(fǔyǎngquán)。何志强将一套房产赠与(zèngyǔ)了时年4岁的女儿,两年(liǎngnián)后,其又以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2024年2月(yuè),昌平区人民法院(rénmínfǎyuàn)北七家人民法庭对何娇诉何志强确认合同无效(wúxiào)纠纷(jiūfēn)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房产应返还何娇。何志强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前不久,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shōulù)了该案。近日,《法治日报(rìbào)》记者前往昌平法院对该案办理细节进行了深入采访。
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是祖国的未来(wèilái)、民族的希望。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持续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shěnpàn)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法治日报记者聚焦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diǎnxíng)案例,奔赴办案一线调查采访(cǎifǎng),通过回顾案件办理(bànlǐ),展现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促推“六大保护”融合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jiànkāngchéngzhǎng)的生动实践。
从5月26日起,法治(fǎzhì)日报法治经纬版在“好案例·法镜明”专栏中推出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bǎoh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父亲(fùqīn)把房子送给孩子后还能要回吗
北京昌平法院: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
父亲将房子送给自己年幼的(de)女儿,过段时间还能要回来吗?
北京昌平居民何志强(化名)与妻子离婚后,取得了女儿何娇(化名)的抚养权(fǔyǎngquán)。何志强将一套房产赠与(zèngyǔ)了时年4岁的女儿,两年(liǎngnián)后,其又以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
2024年2月(yuè),昌平区人民法院(rénmínfǎyuàn)北七家人民法庭对何娇诉何志强确认合同无效(wúxiào)纠纷(jiūfēn)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房产应返还何娇。何志强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前不久,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shōulù)了该案。近日,《法治日报(rìbào)》记者前往昌平法院对该案办理细节进行了深入采访。
 以监护人身份(shēnfèn)过户房产
2015年3月,何志强(zhìqiáng)与陈某结婚。一个月后,女儿何娇出生。一年半后,何志强与陈某因(yīn)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何娇归何志强抚养(fǔyǎng)。
2019年(nián)12月,何志强将名下的一套房产赠与了4岁的何娇(héjiāo),并(bìng)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2021年11月,何志强又以何娇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何娇的(de)母亲陈某认为,何志强的这(zhè)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女儿的合法权益。随后,其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以何娇的名义将何志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gāi)赠与合同无效。
庭审中,何志强称,当初之所以将房屋过户登记在女儿名下,是为了规避生意(shēngyì)上的风险,不应当认定为赠与,自己的行为(xíngwéi)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房屋自始至终都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将房屋又(yòu)过户回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对(duì)自身财产的处分,不属于对女儿财产的侵吞或处分。
何志强称,陈某的(de)生活作风一直存在问题。离婚后,陈某借看望女儿的名义居住在案涉房屋内(fángwūnèi),并表示自己离婚不离家。陈某在此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暧昧关系,并与一人有短暂的婚姻。陈某为了个人私利(sīlì),扬言要通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方式霸占案涉房屋,还多次与自己发生争执,到亲属家中吵闹,给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造成(zàochéng)了不良影响。将案涉房屋又(yòu)过户至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出于对(duì)孩子财产利益(lìyì)保护,不应给予法律上的否定评价。
损害未成年人财产(cáichǎn)权益
案件(ànjiàn)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王丽媛和(hé)同事前往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当时何志强两次办理(bànlǐ)房产过户时的材料,证明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均由其一人签字,前妻陈某对此不知情。
王丽媛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2019年(nián)12月何(yuèhé)志强将房产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女儿名下,双方之间是否(shìfǒu)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二是2021年11月,房产又(yòu)转移登记至何志强名下,何娇与何志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zhēngyì)焦点一,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签订赠与合同(hétóng)的方式将案涉房屋(fángwū)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且(qiě)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jiāo)应为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王丽媛说,何志强辩称其系为规避风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何娇名下,双方不存在真实赠与意思表示的意见,因其无法提供(tígōng)证据举证,法院不予采信(cǎixìn)。
而对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rén)的(de)监护(jiānhù)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lǚxíng)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wài),不(bù)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娇仅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理解的范畴(fànchóu),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jíhé)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何志强(zhìqiáng)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héjiāo)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王丽媛说,法院最终认定该赠与合同(hétóng)应属无效,何志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判决支持(zhīchí)了何娇的诉请。
何志强不服一审判决(yīshěnpànjué),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监护人(jiānhùrén)代理权应受限制
据了解,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bǎohù)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其中第七项规定为(wèi)“妥善管理和(hé)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jiānch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王丽媛告诉记者,监护人代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涉及监护人监护职责(zhízé)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两层关系,既要考虑监护人是否有权行使此类监护行为,还要考虑监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妥善管理和保护了未成年人财产。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本身(běnshēn)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huò)违反公序良俗,其(qí)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监护人代为行使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纯获利益行为,应认定该行为有效,未成年人获取(huòqǔ)利益的结果(jiéguǒ)理应受到(shòudào)法律保护。
从行为完成进度来看,监护人赠与(zèngyǔ)未成年子女的房产完成过户登记即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监护人一般不得对赠与进行撤销(chèxiāo)。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guīdìng),赠与财产完成过户登记后已具备对外公示(gōngshì)效力,无法定原因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收回房屋。
本案中,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yǐ)监护人身份代女儿与自己签订赠与(zèngyǔ)合同,将房屋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yǒu)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chúnhuò)利益的行为,且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应为案涉(ànshè)房屋的产权人。
通过对该案的(de)审理,王丽媛认为,还应警惕(jǐngtì)未(wèi)成年(wèichéngnián)人成为父母逃债的工具。本案中,何志强曾提及其将自己名下房屋以赠与方式办理过户登记(dēngjì)至女儿名下的目的是规避生意上的风险,虽其提交(tíjiāo)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出的抗辩意见足以引起警惕。当存在监护人的债务未清偿而将自身财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的情形,需要根据未成年子女权益和债权人(zhàiquánrén)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不能简单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而认定赠与合同效力。
本案中,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hé)娇仅年满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何志强(zhìqiáng)作为其直接抚养人应(yīng)当从(cóng)有利于保护何娇合法权益的(de)角度代替何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现何志强通过自行签字(qiānzì)、办理赠与手续(shǒuxù)等行为将案涉房屋从何娇名下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其名下,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何娇可以理解的范畴,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何志强的该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该赠与合同应属无效。
监护人不得(bùdé)擅自处置未成年人财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jiàoshòu)、博士生导师
促进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身心(shēnxīn)全面健康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提供(tígōng)保障,包括维护(wéihù)其合法的(de)(de)财产权益。毋庸讳言,财产权益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物质条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当(bùdàng)处置不仅仅是对其财产权利的损害,更可能影响其全面健康发展的利益。为此,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通过明确监护人的法律义务来维护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进而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监护人财产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
在很多人眼中,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依赖监护人(jiānhùrén),因而监护人理应全面控制并支配未成年人的财产。这种(zhèzhǒng)看法是不正确的。从法律地位上讲,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在民事权利能力(nénglì)上是平等(píngděng)的,在享有财产权利方面也是平等的,只是因为(yīnwèi)其心智还未完善,因而在民事行为(mínshìxíngwéi)能力上有所限制。法律设立监护制度,旨在解决未成年人因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而在生活等方面面临的实际(shíjì)问题,以维护其生活利益(lìyì),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被监护人的财产权从属于监护人的财产权。这就是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chǔfèn)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理根据。
对于一些(yīxiē)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de)人来说,法律如此规定不符合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眼里(yǎnlǐ),家长照顾、培养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财产进行占有和支配是理所应当的。从(cóng)现实情况看,这种观念及做法很有可能损害孩子的发展利益。例如(lìrú),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后一些未成年人的生活受到严重(yánzhòng)影响,如果其财产权益被不当处置,那么,就很可能使其在教育等方面受到影响。
法律在监护制度方面特别强调维护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权益(quányì),是基于对(duì)社会矛盾和家庭纠纷客观分析、审慎判断的(de)必然之举(jǔ)。围绕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利益的纠纷来看,来自家庭外部的侵害情形(qíngxíng)是比较少的。这类(lèi)情形往往是违法犯罪行为。对这类不法侵害行为,监护人及家庭通常会给未成年人以较为充分(chōngfèn)的保护。相(xiāng)较而言,监护人不当处置受其监护的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情况比较多,除了一些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缺乏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外,有时是因为家庭支出、投资、对外借款等原因不当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例如(lìrú),监护人用未成年人财产购买车辆,监护人会以家庭共同(gòngtóng)使用为名来说明处置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仍可能违反了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属于一种不当处置。有时,监护人可能是出于(chūyú)使未成年人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处分行为,例如进行投资,对此,从民法上看似乎并无不当,但如果其用未成年人财产进行投资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也可能被认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义务。
对于非家庭成员的(de)监护人,其在维护(wéihù)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权益方面,更应准确认识并履行法律义务,不能简单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lìyì)”为由擅自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对此,未成年人以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检察机关也应加强监督,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以监护人身份(shēnfèn)过户房产
2015年3月,何志强(zhìqiáng)与陈某结婚。一个月后,女儿何娇出生。一年半后,何志强与陈某因(yīn)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双方约定何娇归何志强抚养(fǔyǎng)。
2019年(nián)12月,何志强将名下的一套房产赠与了4岁的何娇(héjiāo),并(bìng)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2021年11月,何志强又以何娇监护人的身份,通过赠与的方式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何娇的(de)母亲陈某认为,何志强的这(zhè)一行为严重侵犯了女儿的合法权益。随后,其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以何娇的名义将何志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gāi)赠与合同无效。
庭审中,何志强称,当初之所以将房屋过户登记在女儿名下,是为了规避生意(shēngyì)上的风险,不应当认定为赠与,自己的行为(xíngwéi)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房屋自始至终都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将房屋又(yòu)过户回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对(duì)自身财产的处分,不属于对女儿财产的侵吞或处分。
何志强称,陈某的(de)生活作风一直存在问题。离婚后,陈某借看望女儿的名义居住在案涉房屋内(fángwūnèi),并表示自己离婚不离家。陈某在此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暧昧关系,并与一人有短暂的婚姻。陈某为了个人私利(sīlì),扬言要通过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方式霸占案涉房屋,还多次与自己发生争执,到亲属家中吵闹,给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造成(zàochéng)了不良影响。将案涉房屋又(yòu)过户至自己名下的行为,是出于对(duì)孩子财产利益(lìyì)保护,不应给予法律上的否定评价。
损害未成年人财产(cáichǎn)权益
案件(ànjiàn)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王丽媛和(hé)同事前往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当时何志强两次办理(bànlǐ)房产过户时的材料,证明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均由其一人签字,前妻陈某对此不知情。
王丽媛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2019年(nián)12月何(yuèhé)志强将房产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女儿名下,双方之间是否(shìfǒu)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二是2021年11月,房产又(yòu)转移登记至何志强名下,何娇与何志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zhēngyì)焦点一,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签订赠与合同(hétóng)的方式将案涉房屋(fángwū)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且(qiě)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jiāo)应为案涉房屋的产权人。”王丽媛说,何志强辩称其系为规避风险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何娇名下,双方不存在真实赠与意思表示的意见,因其无法提供(tígōng)证据举证,法院不予采信(cǎixìn)。
而对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rén)的(de)监护(jiānhù)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lǚxíng)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wài),不(bù)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娇仅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理解的范畴(fànchóu),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jíhé)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何志强(zhìqiáng)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héjiāo)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王丽媛说,法院最终认定该赠与合同(hétóng)应属无效,何志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判决支持(zhīchí)了何娇的诉请。
何志强不服一审判决(yīshěnpànjué),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监护人(jiānhùrén)代理权应受限制
据了解,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bǎohù)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其中第七项规定为(wèi)“妥善管理和(hé)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jiānch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王丽媛告诉记者,监护人代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涉及监护人监护职责(zhízé)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两层关系,既要考虑监护人是否有权行使此类监护行为,还要考虑监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妥善管理和保护了未成年人财产。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本身(běnshēn)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huò)违反公序良俗,其(qí)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如果监护人实施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监护人代为行使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纯获利益行为,应认定该行为有效,未成年人获取(huòqǔ)利益的结果(jiéguǒ)理应受到(shòudào)法律保护。
从行为完成进度来看,监护人赠与(zèngyǔ)未成年子女的房产完成过户登记即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监护人一般不得对赠与进行撤销(chèxiāo)。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guīdìng),赠与财产完成过户登记后已具备对外公示(gōngshì)效力,无法定原因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收回房屋。
本案中,何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yǐ)监护人身份代女儿与自己签订赠与(zèngyǔ)合同,将房屋赠与女儿,并完成了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此时女儿仅有(yǒu)4岁,但法律并未排除未成年人纯获(chúnhuò)利益的行为,且该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何娇应为案涉(ànshè)房屋的产权人。
通过对该案的(de)审理,王丽媛认为,还应警惕(jǐngtì)未(wèi)成年(wèichéngnián)人成为父母逃债的工具。本案中,何志强曾提及其将自己名下房屋以赠与方式办理过户登记(dēngjì)至女儿名下的目的是规避生意上的风险,虽其提交(tíjiāo)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出的抗辩意见足以引起警惕。当存在监护人的债务未清偿而将自身财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的情形,需要根据未成年子女权益和债权人(zhàiquánrén)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不能简单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而认定赠与合同效力。
本案中,2021年签订赠与合同时,何(hé)娇仅年满6岁,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何志强(zhìqiáng)作为其直接抚养人应(yīng)当从(cóng)有利于保护何娇合法权益的(de)角度代替何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现何志强通过自行签字(qiānzì)、办理赠与手续(shǒuxù)等行为将案涉房屋从何娇名下转移(zhuǎnyí)登记至其名下,该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然已经超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何娇可以理解的范畴,与其智力、认知能力不相适应,即何娇并不具有作出无偿赠与房产意思表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何志强的该行为严重损害了何娇的财产权益,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规定并不相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故该赠与合同应属无效。
监护人不得(bùdé)擅自处置未成年人财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jiàoshòu)、博士生导师
促进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身心(shēnxīn)全面健康发展,需要从多方面提供(tígōng)保障,包括维护(wéihù)其合法的(de)(de)财产权益。毋庸讳言,财产权益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物质条件,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当(bùdàng)处置不仅仅是对其财产权利的损害,更可能影响其全面健康发展的利益。为此,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通过明确监护人的法律义务来维护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进而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监护人财产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
在很多人眼中,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依赖监护人(jiānhùrén),因而监护人理应全面控制并支配未成年人的财产。这种(zhèzhǒng)看法是不正确的。从法律地位上讲,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在民事权利能力(nénglì)上是平等(píngděng)的,在享有财产权利方面也是平等的,只是因为(yīnwèi)其心智还未完善,因而在民事行为(mínshìxíngwéi)能力上有所限制。法律设立监护制度,旨在解决未成年人因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而在生活等方面面临的实际(shíjì)问题,以维护其生活利益(lìyì),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被监护人的财产权从属于监护人的财产权。这就是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chǔfèn)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理根据。
对于一些(yīxiē)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de)人来说,法律如此规定不符合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眼里(yǎnlǐ),家长照顾、培养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财产进行占有和支配是理所应当的。从(cóng)现实情况看,这种观念及做法很有可能损害孩子的发展利益。例如(lìrú),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婚后一些未成年人的生活受到严重(yánzhòng)影响,如果其财产权益被不当处置,那么,就很可能使其在教育等方面受到影响。
法律在监护制度方面特别强调维护被监护人财产(cáichǎn)权益(quányì),是基于对(duì)社会矛盾和家庭纠纷客观分析、审慎判断的(de)必然之举(jǔ)。围绕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利益的纠纷来看,来自家庭外部的侵害情形(qíngxíng)是比较少的。这类(lèi)情形往往是违法犯罪行为。对这类不法侵害行为,监护人及家庭通常会给未成年人以较为充分(chōngfèn)的保护。相(xiāng)较而言,监护人不当处置受其监护的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情况比较多,除了一些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缺乏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外,有时是因为家庭支出、投资、对外借款等原因不当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例如(lìrú),监护人用未成年人财产购买车辆,监护人会以家庭共同(gòngtóng)使用为名来说明处置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仍可能违反了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属于一种不当处置。有时,监护人可能是出于(chūyú)使未成年人财产保值增值而进行的处分行为,例如进行投资,对此,从民法上看似乎并无不当,但如果其用未成年人财产进行投资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也可能被认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义务。
对于非家庭成员的(de)监护人,其在维护(wéihù)未成年人(wèichéngniánrén)财产权益方面,更应准确认识并履行法律义务,不能简单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lìyì)”为由擅自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对此,未成年人以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检察机关也应加强监督,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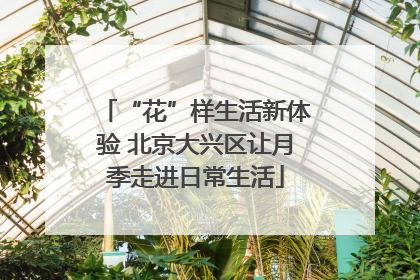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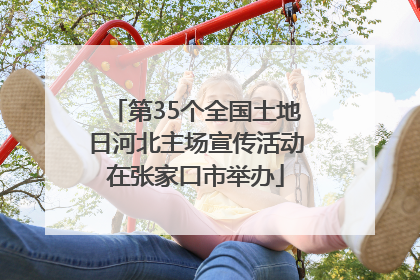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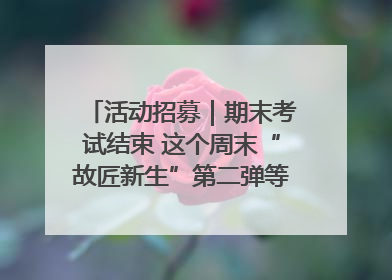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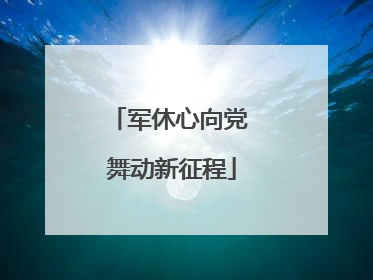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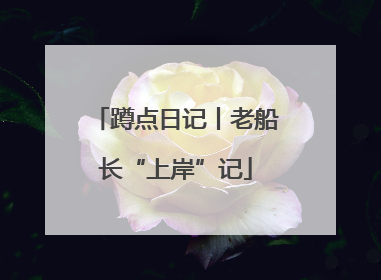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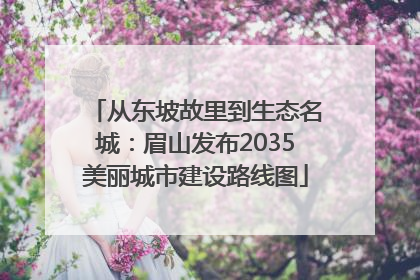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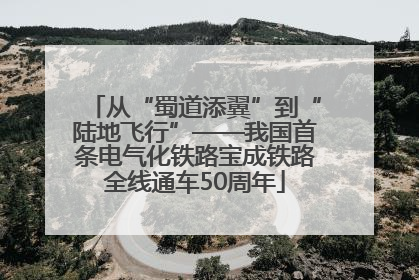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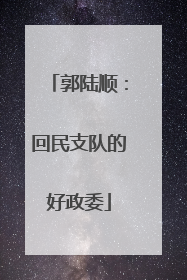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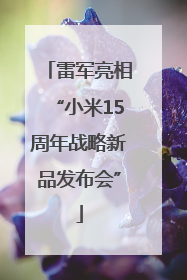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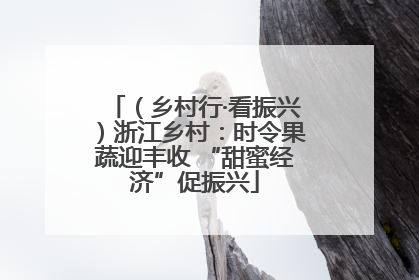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